50岁之后,我开始为“第二职场”奔波
2025-07-21 22:25:53 · chineseheadlinenews.com · 来源: 极昼story

随着国内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2年至203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将有2000万人退休。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退休后重返职场。对他们来说,工作不仅是维持经济来源的必要手段,也是一种与社会保持连接、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但真正退休后,他们才发现,求职路上处处是关卡——
年龄是最难逾越的门槛。此外,他们能选择的岗位也十分有限,即使曾在外企、医院或政府单位工作的中老年人,重新找工作时也难逃重重筛选:天平两端,一边是希望找到体面稳定、被真正接纳的工作的老年人;另一边,大量强度高、保障少、薪资低的岗位长期空缺,无人问津。
文丨魏芙蓉 蔡家欣
编辑丨王一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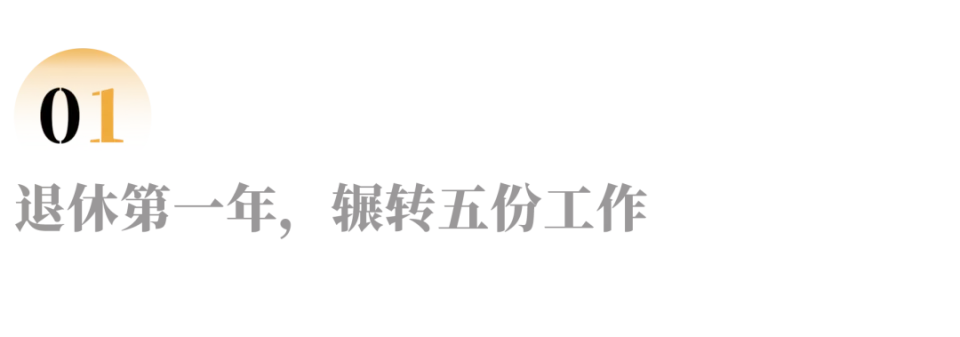
55岁的陈英敏没想到,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再踏入职场,会如此艰难。
她原本在一家外企做生产管理,月薪七八千。2023年12月正式退休后,她没打算歇着,早早开始做准备:提前几个月泡在招聘网站上,每天刷岗位、投简历,想着能无缝衔接上新工作。
准备做得充分,可真正退休那天起,她才发现,这个年纪找工作就像“打怪升级”,处处是关卡。
第一份新工作是在一家幼儿园。和她过去的工作内容毫无关系,但已经算是“相对理想”的机会。三个老师照看四十多个孩子,她和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并肩作战——早上通风消毒,逐一检查孩子的进食、饮水、盯孩子如厕、清理卫生……几乎没机会坐下。干了几个月,她就撑不住了。
之后,她又陆续换了几份工作。在小米授权店做售后时,赶上夏季高峰,安装订单激增,她一天站11个小时,连喝水、上厕所都顾不上。一个月挣了4600元,但身心已经到了极限。
辗转去到的仪器厂、服装厂也不顺利。仪器厂强度太大,服装厂里好不容易找到份办公室文员的岗位,她干了十几天,对方一句“不需要人了”,又被辞退。
她还尝试过做销售——面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驼奶。因为心理压力大,也没坚持多久,“我这个人比较诚实,不会忽悠人。”
最焦虑的时候,她甚至在QQ群里接下一份“刷单”的活儿,想补贴点家用,结果被骗了一万多元。
退休这一年,陈英敏渐渐意识到,想再找到一份朝九晚五、双醒倘定的工作,几乎成了奢望。去年一整年,她像流水线上一个不断被传送的零件,不停换岗、重新上手,一年内换了五份工作,大多只做了一两个月,最短的一份,仅坚持了十几天。

●图源东方IC
在上海,51岁的张芹也在为退休后的“第二职场”奔波。和陈英敏不同,她从一开始就降低了预期。她很清楚,到了这个年纪,精力和体力都不比从前,每天要睡足十小时,已经无法承担高强度体力劳动。过去她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做运营管理,月薪9000多元;退休后,只希望找份相对轻松的工作,每月挣四五千,加上退休金,刚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
可现实比她预想中残酷得多。简历投出去,不断被泼冷水。她发现,招聘平台对她这样的中老年求职者并不友好:可投的岗位集中在所谓的“吉祥三保”——保洁、保安、保姆;很多岗位说明里常写着“限50岁以下”,有些甚至只接受48岁以下。她刚退休就已被挡在门外。
她曾去麦当劳面试,那里长期招聘退休人员,对方开出时薪19元,虽说是兼职,排班却接近全职:一周五天、每天工时超8小时。她觉得强度太高,待遇又低,权衡之后还是选择放弃。其实只要不涉及重体力劳动,她大部分工作都愿意尝试,但“反馈几乎为零”。
像陈英敏和张芹一样,越来越多的老人希望在退休后继续工作。据国家统计局预测,2022年到2031年间,每年约有2000万人退休。一家招聘网站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也显示,近七成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
但现实并不乐观,适合老年人的岗位稀缺,且多数工作强度较大。许多老人不会使用招聘软件,甚至连投递简历的渠道都难以找到。社交平台上,子女替父母找工作的帖子也不少。
2023年年底,上海的徐女士就曾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她的妈妈原本在云南做警察,退休后搬到上海跟她同住,也想找一份简单、稳定、能早点下班的工作,哪怕工资不高也没关系。
帖子发出去后,有人建议可以去做人民调解员,但打听下来发现需要本地户口。后来她们联系上一家律所的法律援助岗位,负责处理邻里纠纷和社区事务。妈妈此前做过类似工作,经验不缺,但因为普通话不够标准,又不是本地人,一个月后还是辞了,“总觉得干不顺。”
为尽快上岗,徐女士还加了不少帮退休老人找工作的群,一看全是保安、保洁、绿化、红娘之类的岗位。她替妈妈筛了一轮:绿化太累、干不动;红娘靠抽成、没底薪,只能试试保洁。
其实妈妈一开始是抗拒的,总觉得“不太体面”,但又别无选择。她们没想到,这份看似没门槛的工作,妈妈竟然也没应聘上。对方没说原因,她们猜,或许是因为老人当过警察,让人觉得“不好管”。
上网发帖前,徐女士就预料到帮妈妈找工作不会轻松。如今就业形势紧张,多少年轻人都为工作发愁,更别说上了年纪的。但这个结果还是让两人很受打击,“就算把心态放低了,外面的环境也未必接得住。”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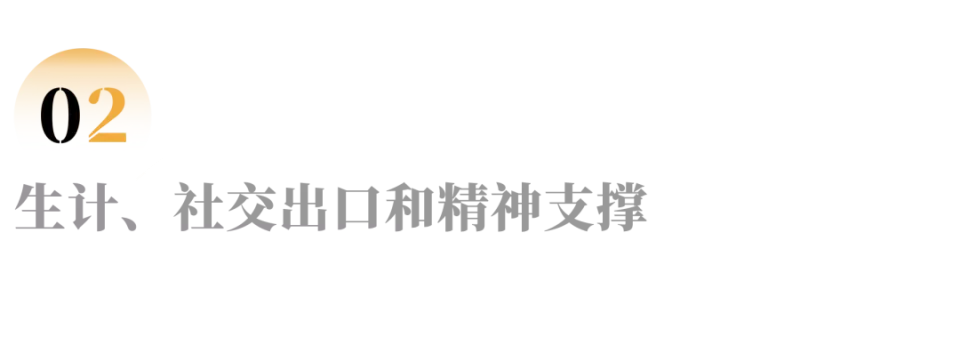
很多老年人选择退休后重返职场,最直接的原因,是现实的经济压力。陈英敏的焦虑,在退休前就开始了。她算过一笔账:家里的水电、物业每月一千多,儿子还在上初三,学杂费也要一千多,再加上日常开销,每月生活成本至少三四千元。她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出头,丈夫的收入大部分要拿去偿还老家盖房时留下的外债。
新疆的康女士也被同样的焦虑压得喘不过气来。她退休那年,女儿升入高三,决定去杭州学艺术,家庭开销突然增加。她每月的退休金远远不够负担。
为了陪读,她随女儿搬去了杭州。几乎刚落脚,就开始找工作。退休前,她是一家公立医院的收费员。退休后,女儿陪着她面试了多个岗位。超市送货员、酒店铺床、餐馆打杂……连饿了么骑手也试过,都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没坚持下去。
接连碰壁两个月,女儿都劝她放弃,“妈妈,现实挺残酷的,要不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养养身体。”但康女士不甘心。
她后来找到一份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月薪3600元,每周休息一天,负责看守柜台、整理货架。每天在货架间来回穿梭,微信步数动辄两万,刚上岗时脚肿了好几天。但她说,对没一技之长、只能靠力气挣钱的老人来说,这种“干净、稳定、不太费劲”的工作,已经算是难得的好工作。
她坚持了半年,直到女儿高考结束,又匆匆返回老家,重新开始找下一份工作。毕竟,女儿接下来还要上大学。

●图源东方IC
除了补贴家用,“停不下来”的习惯,以及希望继续发挥专长,延续职业身份,都是老人们选择重返职场的原因。《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中,近一半受访老年人都表示,再就业是他们继续参与社会、维持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渠道。
张芹是在真正停下来后,才发现无法适应“无所事事”的生活。她去年9月退休,因为身体不适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可没过多久,就开始变得焦虑:“突然跟外界断了联系,像被社会遗忘了。”
她喜欢和年轻人接触,乐于尝试新事物,总希望自己看起来不像个“老年人”。休整半年后,她做了全面体检,确认身体无碍后,立刻开始投简历,“我不怕衰老,但怕脱节。”
退休后生活节奏骤变,精神和心理上的落差不可避免,尤其对那些习惯快节奏生活的人来说更为明显。李洁原本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做财务负责人,她过去频繁出差海外,参加财会行业的研讨会,一直觉得自己“和时代是同步的”。
但疫情后集团改革、人事洗牌,49岁,离正式退休还差一年,她和公司协商办理了提前退休。刚退休那阵,她一度觉得轻松美好:计划旅行、学跳舞、每天睡到自然醒,终于可以过上“向往的自由生活”。
这样的状态并没维持多久。脱离职场后,朋友圈散了、信息断了,生活仿佛一下子“静止”下来。尤其是作为校友被邀请回母校时,老同学们口头上都羡慕她“退休早、很潇洒”,可李洁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和那些仍活跃在职场的人,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话题。
“好像突然没有价值了,有种被淘汰的感觉。”她说,也许是更年期的缘故,情绪更容易起伏不定,经常会莫名沮丧、不甘心。对她来说,工作不仅是经济来源,更是精神支撑和社交出口,也是延缓衰老的方式。
可即便像李洁这样履历丰富、专业背景扎实的资深财务,真正开始找工作后,还是频频碰壁。她发现,退休的求职者仿佛自动被贴上了“能力退化”的标签。过去多年,她的简历只要挂在网上,猎头自然会找上门;而如今,有猎头坦率告诉她,“你的资历是非常qualify(资深)的,但年龄过了,这是‘硬性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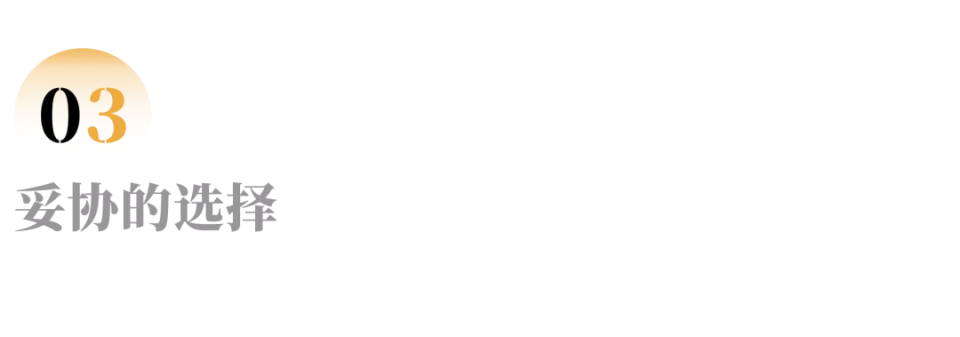
有适合老人的工作吗?运营一个专为中老年人服务的求职账号,陈武每天都会在后台收到大量老人的私信。
陈武是一位互联网产品经理,今年初在帮临近退休的父母找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庞大需求。后来他成立项目专门注册账号,每天从各大平台搜集、筛选适合岗位,整理成“老年人就业信息合集”发布。
来咨询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有人想找全职,有人一边带孙子,一边想找份补贴家用的兼职。他们中大多没有一技之长,也说不清自己能干什么。介绍自己时,常是一句简单的总结:吃苦耐劳,会照顾孩子,会做饭。
求职需求旺盛,但对应的岗位却极其有限。浏览和整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后,陈武发现,有技能的老人或许还有返聘机会,但对大多数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来说,可选的仍是“三保”类岗位,或是超市理货、仓库管理员、园林绿化等基础性工作。
而且即便是这些岗位,如今的年龄门槛也在收紧,年过五十就难有竞争力了。
年龄常常成为老人求职过程中难以逾越的“硬门槛”。在东北长期从事招聘的人力资源顾问张铎萧指出,背后最关键的原因是保险。很多企业不会为退休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取而代之的是商业意外险,这类保险对投保人年龄限制极严,大多卡在55岁或65岁以内,超过年龄就无法投保,企业用人也就受限。这成为招聘中最现实、也最难绕开的障碍。

●图源东方IC
张铎萧曾为多家企业提供招聘解决方案,从技术型、管理型岗位,到物业公司招“三保”类等基础职位,都涉及到退休老人的就业安置。
其中地产、环保、消防等咨询服务类岗位偏好有行业经验的老人,洗浴、KTV等线下娱乐行业,往往更愿意招揽那些有人脉、有行业积累的退休员工;而像“三保”类的大部分岗位,企业招录退休人员往往是无奈之选——在“年轻人难招、岗位吸引力不足”的前提下,企业只能退而求其次。
筛选这类应聘者时,企业的考量远不止年龄。思维清晰、沟通顺畅是基础,其次是履历背景。如果面试者退休前职务过高,张铎萧一般会婉拒:“一来他不太可能真做,(或许)只是心血来潮,干一段时间就走,又得重新招人。”像徐女士妈妈这样有公务员背景的人来应聘保洁岗位,他也倾向于回绝——企业更看重的是稳定性和招聘成本。
此外,企业还会尽力避免一些“极端风险”。张铎萧回忆,疫情那几年,他负责的物业项目里,每个月都有老年员工因工伤或突发疾病去世,需要处理赔付——尤其在保洁、保安等体力岗位上,这类情况更为常见。
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老年人时会格外谨慎,要求提供三个月内的体检记录,甚至,为了防范一些“倚老卖老的碰瓷行为”,查征信、流水和犯罪记录都成了现在招聘的常规操作。
老人找工作难,作为招聘方,张铎萧也感慨“招人同样难”。在东北,“三保类”岗位的缺口一直很大。张铎萧记得,尤其是2021年前后,恒大地产爆雷,引发一波售楼处“维稳潮”,保安一度成了紧俏工种。
为了完成用工指标,他和团队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试了一遍:电视台、广播、招聘网站轮番上阵。考虑到许多老人不上网,他们又转向线下,大量张贴纸质招聘广告,“贴出去的纸按万(张)算。”
但整体效果很有限。得到的回应都相似:要么身体吃不消,嫌工作太累;有的则直接觉得保洁、保安说出去“不好听”。
在陈武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供给侧”——真正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岗位太少。“三保类”工作,强度大、环境苦,不是所有老人都能胜任;相比之下,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其实是一些轻体力劳动,或者具备灵活工时、能兼顾家庭的岗位形式,比如短时服务、简单文职、辅助类工种等。但这些岗位在国内的市场暴给中仍比较稀缺。
相比之下,已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曾通过立法来保障和拓展老年人的岗位供给渠道,日本最新的《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直至70岁的就业机会,方式包括退休后继续雇佣,外包给关联企业等。
陈武也一直希望能推动国内企业开发出更多“适老化”岗位。过去,他和团队也主动找企业沟通过,看是否愿意专门为老年人设置一些更友好的工种。但真正愿意配合的,往往只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类行业,其他行业大多反应冷淡。
这样的就业市场现状,让原本想帮父母找工作的陈武,在深入了解之后,反而更加迷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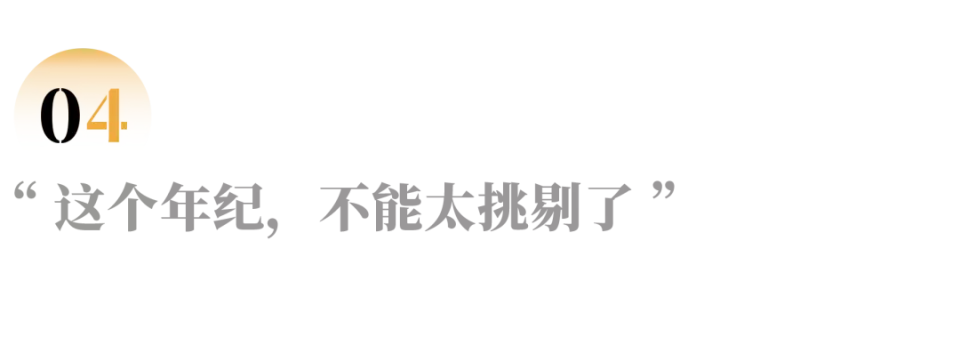
在局限的现实面前,经历几轮求职起落的老人们,只能一边不断下调预期,一边学着接受现实。
辗转五份工作之后,陈英敏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在一家生产厨房台面的工厂,跟进客户的订单,产品的报价、生产、交付等。
这份工作与她退休前的业务流程非常接近,只不过在报酬和休息时间上大打折扣。工资按出勤天数结算,满勤时月薪约4500元,碰上节假日就要缩水——年初春节那个月,她实际只拿到两千多。工作节奏也更紧张,“基本没有双休的概念”。即便下班,只要客户发消息,就得第一时间回复。
尽管如此,这份工作她还是坚持了半年多,是退休后做得最久的一份。“这个年纪,不能太挑剔了。”她说。
曾任财务主管的李洁也有类似的感慨,“要面对现实,你的确不再年轻,能有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找工作时,她把目光转向一些小厂、民企。不少公司看完她的履历后都会迟疑:“我们这个小鲍司,你能适应吗?”她就一遍遍地解释:“我已经调整好了。”
最终她入职了一家小型私企做财务核算。跟她过去在上市公司的经历完全不同:不再有复杂的管理架构,整个公司的财务部只有她一个人,所有核算、付款、记账、报表的活都由她包办。
李洁说,这份工作虽然收入远不如从前,但胜在离家近、无业务压力。她每天散步去上班,一个月的活,一个星期就能做完。换个心态来看,这份工作反而有了某种“性价比”。

●图源东方IC
张芹算是幸运的。就在她准备暂停找工作时,意外收到一家老年健身房的面试邀请。她特地向对方确认:“我是退休的,你知道吗?”没想到HR听完她的自我介绍后,反而说:“完美,太完美了。”
她后来才意识到原因:这是一家政府扶持的健身房,专门为老年人服务,张芹不仅有管理经验,还健身多年,对器械操作十分熟悉,几乎与这份工作天然契合。
入职前,公司安排她体检,还为她购买了灵活用工保险。虽然每月保费不高,但让她觉得“起码上下班路上有点保障”。她说,这是之前面试过的所有岗位里,第一次有人主动提供这些基础保障。
张芹喜欢健身,这份工作恰好可以让她兼顾兴趣和收入。她日常只需要维护器械、协助会员登记、关注使用安全,偶尔也会承担些销售任务,但整体压力不大。每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还能顺便锻炼身体。
但找到工作并不意味着长期的稳定。对他们来说,工作随时可能中断,很多人都在悄悄为“下一步”做准备。
张芹打算先在健身房干一年。如果公司还需要她、自己也干得开心,就继续干;不行的话,也能随时退场。她还得腾出一部分精力给家里——女儿今年30岁,正在备孕,她准备随时帮忙带孩子。“只有这方面能托举她。”张芹说。女儿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太清楚边工作边带娃的辛苦,作为母亲,她希望能再尽点力。
陈英敏也提前做了安排。她报了社工证的培训班,一则广告上说“大龄退休也能考,只要成绩合格就能安排工作”,她心动了,花了几千块报名费,期待着这能成为自己未来的另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