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点金庸、武侠以外的少林寺
2025-07-28 15:26:20 · chineseheadlinenews.com · 来源: 海边的西塞罗
“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这年头的中文互联网,看来是真的是没什么可聊。这两天网传少林方丈释永信被抓,昨天又得到了官方证实。一时间,我关注的公众号,除了继续喊“乌克兰万岁,请大家为正义给我打赏”的,就剩下各种变着花说这个事的了。
可是看来看去,所有人在聊少林寺的时候,金庸的影子,大家贴出港版《天龙八部》里鸠摩智去砸场子时的名言:“少林寺,原来是一个暗藏春色、藏污纳垢之所!”高呼金庸先生神预言,还调侃道:“少林寺上次出事还是在北宋。”

但实际上,这话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港剧版鸠摩智的暴论不是《天龙八部》里的原话,金庸没写这一出。第二,就算少林寺玄慈方丈和叶二娘的那点事儿,也是金老爷子自己改编出来的。历史上的少林寺方丈,一般还没玩的这么惊世骇俗。或者说永信方丈高于艺术、也创造了历史。
我觉得吧,一个六神老师遇事聊金庸,蛮有意思的。大家都没别的话说,纷纷去抢六神老师的饭碗,这挺荒诞的,金庸和泽连斯基养活了中国多少自媒体人啊。
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上上次少林寺“出事”绝对不用追溯到在北宋年代,追溯到距今不远的特殊年代就可以了。
想当年,少林寺因拥有大量土地(民国时期高达1370余亩),被定性为“庙产地主阶级”。僧人根据个人行为被划分为地主、恶霸或贫农。寺院土地被没收分给农民,大部分僧人还俗,仅剩14名无家可归的老弱僧人留守,并被收编为“登封县城关公社郭店大队第23生产队”——后来干脆解散掉了,连少林寺的名号也没留下了来。
至于少林寺“古刹重光”那也是等到特殊年代结束以后,释永信他师父释行正方丈在1979年带领少数僧众回到少林寺,重建东、西禅堂,最开始也非常破败,直到1982年内地与香港合拍的《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少林寺的行情才好了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释永信的商人敏锐可能早于他的佛缘就开始呈现了——少林寺1982年止跌回稳,他是1981年以16岁的年纪遁入空门的。并在入门仅仅六年后就受命于师父玄慈方丈成为一寺主持,22岁就当上了CEO啊,想想我们大家,那都是大学可能还没毕业的年纪。
只能解释为,道德败坏、不守清规戒律固然是一方面,释永信在眼光和能力方面确实有不同常人之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国人城市里还留恋体制内铁饭碗、农民胆子大一点的搞包产承包、胆子再大一点的下海经商做生意。谁在那个年头能想得到跑到少林寺去剃度出家,并在寺里发挥经营才能,六年当上主持呢?
这就是商业智慧啊。

而1987年以后,就是释永信打造他的“少林商业帝国”的故事了,应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释永信也是很精明的。与港台武侠热所打造的少林寺就是个人型高达训练基地、有什么十八铜人、易筋经不同。其实少林寺在宣传中一直用的是两张名片——“功夫圣地”是不假,但更强调也实则更重要的另一张名片是“禅宗祖庭”。与到华人、欧美社会就聊功夫的事不一样,少林寺团队到佛法一直延续的日本,主要亮的就是“禅宗祖庭”这个身份,当然日本和尚是喝酒吃肉娶媳妇都可以的,只要合法就行,咱也不知道释永信老师是不是屡次访日期间见多识广搞得自己心理不平衡了。
话说回来,其实与虚无缥缈的“功夫圣地”不同,“禅宗祖庭”真的是能让少林寺留在历史上写一笔的真正要点。只因“功夫”“武侠”崇拜少林的人,其实大多没什么“佛缘”,甚至还有点唯力畏强的思维习惯,觉得黑暗森林、弱肉强食么,能打就是一切。但实际上,少林寺对中华文明的真正裨益,正是在常被忽略的“禅宗祖庭”之上的。
南梁普通年中(公元520~526年),有一位名叫菩提多摩(达摩)的印度僧人在广州登陆,他自称“佛传第二十八祖”,要来中国传真正的佛法。
当时执政的梁武帝正好崇佛甚至佞佛,曾经数次舍身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要臣子花国库的钱去赎他。看到有这么个“外来的和尚”,还说自己有真佛法,就请来见了一面。
根据禅宗所传《祖堂集》的记载,双方这次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是这样的:
……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师日:“廓然无圣。”
帝日:“对朕者谁?”
师日:“不识。”
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
师日:“无功德。”
帝日:“何以无功德?”
师曰:“此是人天小丙,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
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
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
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北魏)。
这段对话细细分析起来,其实蛮有意思的。南北朝时代,佛教虽然已经在中国流行数百年了,但梁武帝们对佛教的认知依然可能是很粗浅的——你们佛家不是讲因缘果报吗?我一个劲儿的崇佛、我造寺庙、我拼命给钱做财布施,总该算我有功德了吧?
但在佛教尤其是禅宗看来,梁武帝的这些做法其实恰恰不是什么“功德”,因为佛教在印度就是靠反对婆罗门教起家的,婆罗门教忽悠信众顺服的就是这一套——你这辈子生为首陀罗、贱民,没关系,你老老实实遵从摩奴法典,做一颗种姓社会的好螺丝钉,下辈子你投胎转世就当上婆罗门、刹帝利了啊,那吃香的喝辣的、骑在首陀罗头上了。
所以佛教如果把这个东西算“功德”,它就没有超脱于婆罗门教的优势之处。佛教讲的是众生皆苦,你投胎做了婆罗门、刹帝利又怎么样(佛祖释迦摩尼自己就是刹帝利),活一辈子,还是逃不脱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阴炽这八苦,改不了贪嗔痴这三毒,想要真正觉悟解脱,就要“跳出三界外”达成真正的寂静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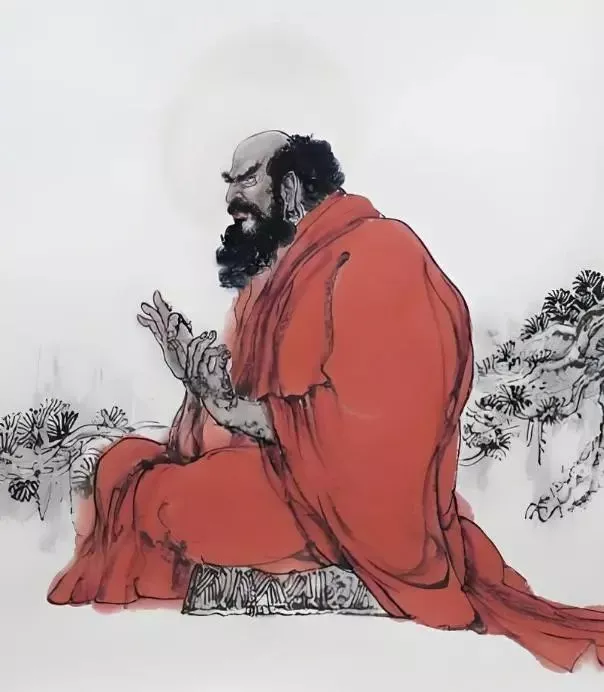
所以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它承认有来世、也“修来世”,但却并不将信仰寄托于来世。这就好比一个996打工人,人生的短期梦想也许可以是“努力工作,跳槽到一个良心企业”,但哪怕去了良心企业,你也是天天上班给人打工,还是苦。最终实现财务自由,天天上班是为了不上班,天天码字是为了不码字,“远离996、007,究竟躺平”,这才是打工人的终极梦想么。
那以这种觉悟再去看梁武帝问达摩祖师的话,就确实有点搞笑。“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这相当于你问单位领导,我天天干活这么拼命,啥时候能像你一样财务自由不上班了——人家领导拿的是股权,不是工资,拿工资你干到死也实现不了财务自由。
所以达摩回答说“此是人天小丙,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你这个东西在后世佛家那里确实不是“功德”,而只是“福德”,福德是指你这辈子做好事、行布施,积些善因,给下辈子或者以后留着用的。这些“有漏因”跟佛家所追求的“究竟涅槃”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福德管的始终只是轮回里面的事。
那怎么才能涅槃呢?怎么才能算有功德呢。这个事儿就是佛教分派别的分水岭了:律宗讲究持律修行、净土宗崇尚念阿弥陀佛、密宗搞了些真言、灌顶之类的东西。而禅宗的主张,就是达摩祖师最后回答梁武帝的那十六个字:“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说白了,就是禅宗主张远离颠倒梦想、摆脱轮回苦境的最终法门,就在每个修行者自己心里,只要你安神定念,达到心一境性也就是禅定的状态,就能从内心深处参悟佛法,而不需要做什么世功、向外求取。
这是一种非常激进、但也的确更接近释迦摩尼“证道”本意的修行方式。但是梁武帝肯定是听不懂的,你想萧衍这个人,他出身宗室,却在皇权的黑暗森林里厮杀半生,好不容易篡权夺位,在尸山血海上建立了大梁朝,你让他吃斋念佛、捐钱建寺这是可以的,毕竟这样都是主动行为。但你让他天天打坐参禅,“不要向外求,向内求”,这跟萧菩萨老爷子执行了一辈子的行为理念严重不符啊。

梁武帝要是这么个闲的住的人,当个不辨马虎的闲散宗室不好么?或者早就在血腥的权力斗争中个给搞掉了,还有机会听你达摩在这里说什么“净智妙圆,体自空寂”?
所以梁武帝闻言马上就变脸了,双方都知道彼此不是一路人,不欢而散。达摩于是之后“一苇渡江”,跑到北魏去传他的禅宗了。
而他最后落脚的寺庙,就是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图破壁”,少林寺最重要的古迹,其实是禅宗初祖修行的那个达摩洞。可惜今天去玩的人一般都在这里匆匆瞄一眼,就跑去看什么“少林武僧救唐王”的武术表演去了。
可从禅宗安家少林一直到隋代的这段时间内,秦制皇权与佛教的博弈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梁武帝那样的皇帝之所以佞佛,也未必真的是多么痴迷于佛法,而是因为南北朝时代以诗书传家的儒家世族的权威实在是太盛了,大到已经足够牵制、掣肘乃至威胁皇权,三国的从司马氏篡政,到东晋时的“王与马,共天下”,再到梁武帝时代,“宇宙大将军”侯景想跟梁武帝求娶世家女子为妻,梁武帝说“我区区一个皇帝,怎么敢替你向世家求亲?你娶个公主凑合一下算了。”所有这些典故都在指向一个问题——以儒家思想武装的世家实在是太尾大不掉了。皇帝想要制约世家,就必须在儒家之外另寻别的思想主张以傍身。
于是他挑上了佛教,还下《断酒肉文》亲自改造佛教,就像同时代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通过皈依基督教并成为其精神领袖以统御罗马一样,梁武帝想的也是通过崇佛来塑造自己的权威。
但是就像达摩说的一样,同时代流行中国的其他佛门宗派过于“世求”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占据的田产、私养的寺妓、名下的佃农,最终成为了世家之外另一个架空皇权的所在。
而与之相对应的,同时代铁血的北朝对佛教走的却是另一条思路。“三武灭佛”中的两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都出在北朝,北朝的统治集团以血腥屠戮的方式不仅夷平了旧世家,而且削平了佛教。相比之下,达摩留下来的“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的禅宗,反而是诸多宗派中对皇权威胁最小、看似最不吵不闹的那个存在。所以每每在灭佛后的废墟上,最先重生,并受到北朝官方默许和鼓励的就是禅宗。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原始积累。
到了隋文帝的时代,少林寺已经做到拥田百倾,僧众数百,名下佃农无数的程度。所谓“少林武术”的传说,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其实在大多数人吃不饱饭的古代农业社会,这世上最有用的“武林秘籍”莫过于“一顿三餐,顿顿吃饱”,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有点余时打熬一下筋骨、锻炼一下身体,会个那么一招半式,到了饿殍遍野,饥民揭竿而起的乱世,这个水平就已经是嘎嘎乱杀的存在了。
虽然少林僧兵在隋末乱世中可能有点战力,在唐玄宗时期留下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其实从来没有记载过“十三棍僧救唐王”之类的故事——李世民那三千玄甲铁骑那是什么战斗力?窦建德王世充几十万联军一起能杀个对穿的存在,他还用得着僧兵去救?
步兵救骑兵、无甲救重甲,一个气死冷兵器发烧友的传说。
少林寺真实的、被唐朝官方承认的功绩,是有十三位僧人参与了唐初平定王世充的战役,具体则是在王世充落败时,活捉了王仁则(王世充侄子)并献给了唐军。
战国时代的日本有个名词叫“落武者狩”,指的就是当地农民或者寺庙僧兵,在武家一场大战结束后,四处打听周围是否有战败的落单武士,确定情报无误后便埋伏在这帮倒霉蛋的必经之路上,待时机成熟便抄起竹枪一拥而上,“不讲武德”地发动“偷袭”老同志。刺死落单武士(落武者),抢走受害者身上的细软铠甲和衣服,再将尸体斩首,以换取死者敌对方的赏金——干掉了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就是这么死的。
参考《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的记载,少林寺僧在隋末乱世里对唐朝的贡献,估计也就是个类似的功劳。

有道是“出家人不打诳语”,十三棍僧“落武者狩”最后是怎么传成“十三棍僧救唐王”咱不得考——就像也有说法认为,达摩祖师可能其实从来没有见过梁武帝,所谓问对都是后世禅宗自己编的,类似北京人老吹牛谁谁我熟。
但是禅宗又是讲“公案”的,公案里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只要“禅意”传达到了就可以。
那以这个标准而论,梁武-达摩问对,面壁十年图破壁、十三棍僧救唐王,可能都是“公案”,这些公案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少林武僧的名号在明代时就越传越神。
明朝有个名将叫俞大猷,有一次从大同镇返京述职的时候特地路过少林寺,点名要看少林寺名扬天下棍法(当时叫剑技),少林寺小山主持不敢怠慢,就招来寺内武术最好的僧人给他演示了一遍。
但看完了以后俞大猷大失所望:就这?就这?这还不如我们军队操练 新兵的入门教学呢!
当然,人家俞大猷毕竟大方面军首长,话出口还是比较委婉:“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以前你们可能有真功夫,只不过现在传丢了吧。
于是小山主持就求俞大猷教点真功夫,俞大猷说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这样吧,你派两个僧人,随我南下从军。
于是少林寺两个僧人就跟着俞大猷当了三年兵,三年后,俞大猷认为这两僧人虽然已得真诀,但武功不算顶尖。可是他们回了少林寺之后,已经是能帮助少林寺武术提升维度的存在了。
从明代正规军实力之海中溅出的一滴水,完全碾压了少林武术;但明军后来又被倭寇和满清八旗碾压,满清八旗后来又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完虐。那觉得少林武术能肉身躲子弹,徒手格洋枪之类的,是不是就过于玄幻了。
武侠世界里,“天下武功皆出少林”,但在真实世界中,回顾少林寺的历史,我们却会发现,“少林武功(甚至荣辱)皆出朝廷”。
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绝对君主、皇权独大的“利出一孔”型社会,皇权不仅垄断了利益与荣誉,更必须绝对控制暴力。所以不会容许少林寺这样一个寺庙拥有什么武林秘籍,教出徒弟动不动以一敌百、敌千,练的跟特种兵一样,这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真要这样,哪个皇帝敢睡的安稳呢?你想干什么?看不把你庙门都铲平了。
所以俞大猷的观察可能才是正确的:少林武术名号虽响,实则跟官军根本不能比——就是要保持这样一个你绝对弱势,说弄你就能弄你的碾压级存在。
天下武术皆出少林,少林荣辱皆出朝廷。武功是少林的、武当的、华山的、峨眉的,但归根结底,都是朝廷的。各路大侠在武侠世界里你争我斗,抢夺不过只是皇权盛宴之后的那么一点残羹冷炙而已。中国历史上更宏大、也更残酷的权力盛宴,金庸们笔下从来没写,写了怕也只会让读者读来丧气——因为跟无比巨大的皇权比起来,连江湖巨无霸少林寺都不过是蝼蚁,个体就更是蝼蚁中的蝼蚁了。
这太残酷了,一点也不浪漫。但这就是历史——真实的中国古代史。
但这才是真正的少林寺吧,没有什么济慈和尚、扫地僧、方证大师,更没有神乎奇迹的《易筋经》等传世武学让僧众们能在乱世中自保。真若说“沧海一小舟”那是这千年古刹里每一个个体,他们的功名荣辱,时刻在那片权欲功名之海上飘荡。
“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达摩祖师说的挺好。
但这苍茫世间、滚滚红尘、如是教法,如此解脱,又终有几人真能做到呢?

全文完
本文6000字,借着释永信出事的事情,写写我眼中的少林寺,搁笔之际我突然想到,上大学那会儿,系里组织去河南游学考察,我还真见过这人一面。
那天我们这些学生在后堂用过斋饭,游戏般的参禅打坐一番,又听了半响禅师讲经(讲的不很好,我旁边一个小沙弥一直在偷偷玩手机,打的是神庙逃亡),最后等到了释永信和我们合影,那是我在小说和电视剧之外见过的第一个方丈。
当时这人给我的感觉,就不像个方外之人,倒更像个商人与官员的结合体。转眼十几年了,不禁感慨系之。
还是要感谢少林寺那天给我们的招待,虽然学校估计是付了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