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和“霸总”,扎堆郑州烂尾楼
2026-01-14 19:26:02 · chineseheadlinenews.com · 来源: 最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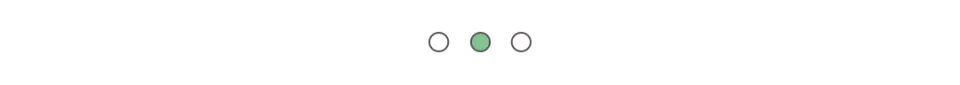
短剧之都
郑州,中国生产短剧最多的城市之一,每月有数百部短剧在这里拍摄、制作,并在一周左右迅速杀青。这是继高速铁路之后的又一“郑州速度”。如果说这里产生了中国荧幕里最多的霸道总裁、富家千金,软饭老公,家产争夺战,应该不算夸张。当然,作为一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要在其中一眼分辨出“短剧工厂”的痕迹,也没有那么容易,换句话说,需要一点点内行人的眼光:对于一位剧组司机来说,依维柯成了一种新的标识,它装着一车一车衣服、道具和演员,游走在郑州的城市和边缘。他对短剧的体认朴素而直观:“外面有多少依维柯,里面就有多少剧组。”
“短剧把郑州的烂尾楼给带起来了,各种样板间全用上了。”一位短剧导演这么说,无人问津的郊区别墅适合拍豪门恩怨,空无一人的售楼大厅可以改造成“集团总部”,几百块一天就能租一套无人入住的小区单元迅速置景,一个剧组拍完,下一个已经等在门口。曾经火热的郑州楼市,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短剧里重获生机。一位剧组外联找到了最好的拍摄地:停业的某房产公司,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而另一个大型的烂尾工程,据媒体报道,即将改造成影视小镇。普通人的生活也被扰动了,开出租车的大姐,看着自己那辆开了60万里程的出租车被贴上“江A”牌照——她的车被剧组租用了。短剧里神秘的“江A”“海A”原来是豫A,她觉得怪好笑。
数据是最好的说明,2024年,郑州制作微短剧的企业超过800家,它们一共承制了3194部微短剧,占全国产量近四成,这个数字在2025年只用三个季度就超越了。郑州,这个原来因富士康而闻名的密集型劳力之城,如今在摄影机里找到了新的定位,在《郑州市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工作实施方案(2025—2027年)》中,郑州市政府提出要将郑州打造成“微短剧创作之都”。

郑州聚美空港竖屏电影基地
但喧嚣也有另一面,2025年10月中旬,44岁的副导演高俊在郑州猝死。据他的妻子说,拍摄期间,丈夫日均工作17小时。
短剧行业的高强度早已不是秘密,以极低的成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制作,天然要求对人力的高效运用,换一个词,就是“卷天卷地”。一位64岁的短剧演员告诉我,有一回他连拍了26个小时。血压也高了,心脏开始突突。他跑去找导演:“一天让我睡两个半小时,今天是第四天了。你想让我这老家伙死了。”导演只是回他:“别说你这老家伙受不了,我这小家伙都受不了了。”
在郑州,近4万的短剧从业者,就是这么劳心劳力地制作着短剧——这一近年来最具吸金能力、也最引人争议的“内容消费品”:2024年,中国短剧的市场辨模已经超过了中国电影票房。
2025年下旬,我来到郑州,入住了一家“短剧酒店”,这家靠近机场的偏僻酒店在今年5月被短剧公司承包下来, 在酒店的会议室,五颜六色的剧本到处散落,一种被“用完即弃”的即视感。我看见诸如“偷生龙凤胎跑路”“冰山总裁的软饭老公”“跟未来孙子视频后找到了亲生子”,很难想象中文还可以这样组合。翻开一页,剧本里赫然写着“美女总裁公开示爱年轻保安”。这部短剧不仅保留传统霸总元素,也紧跟时代潮流,剧里的擎科集团作为“国内人工智能第一股”,接受着来自“战部”的订单。
讨论到底是谁在消费这些神奇的故事,似乎已经过时了,毕竟存在即合理。而人们对制作它们投入的热情也不难理解,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就会奋不顾身,这也不言自明。但我依然好奇,在郑州,这座短剧之都,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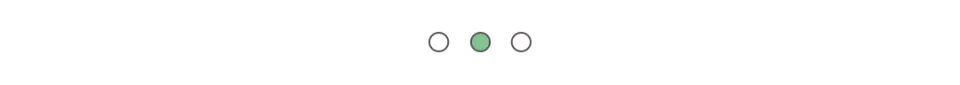
金扁担
此刻,6点58分,天还没大亮。我站在新郑市薛店镇一家酒店楼下,手里被塞了一把没点燃的香——不知道是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还是为了省钱。人们排排站好,脖子都缩在羽绒服里,嘴里呼着白色的气,前后左右参拜,保佑开机顺利,新剧大爆。每个人都拿到了开机红包,里面是一张2块钱的超级大乐透。前一阵郑州短剧圈里流出传言,说一位群演从收到的开机红包里开出了166万大奖。随后有人特意跑到彩票销售点核实,发现这事压根不存在。但金子捏造的假话总是流传千里,隔天我就看见一位群演在朋友圈晒出开机红包,配文是:“166w”。

聚美空港竖屏电影基地,一部短剧正在举行开拍仪式。?视觉中国
而我拿着手中的2块钱大乐透,仔细对比过中奖号码后,发现没有一个数字能对上。
站在我旁边的男生23岁,瘦瘦长长的。曾经是个舞蹈演员,还上过春晚。因为收入拮据,被朋友带着来学做副导演。他悄声地说:“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这部短剧的导演同意我在拍摄时旁观,他有一张圆圆的脸,长得像动画片里的面包超人。把不多的头发留长并扎起来,是他混迹影视行业多年的经验:没有一点“个性”,容易被别人当成小孩子。他说话总是温言软语,笑眯眯的,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轻。直到我亲眼目睹他在片场破口大骂,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对敷衍的道具师和木头一样的演员喊:“别逼我叼你啊!”那一刻我相信,如果不是无戏可拍,他一定是可塑性极强的演员。
从业十多年,这是面包超人导演第一次抓住风口。他曾经做过演员,因为外形不够出色,没能出头。拍过网络大电影,又拍每集十几分钟的横屏中剧,风口就那么短,项目夭折了几个,一年到头紧巴巴地过日子。直到短剧到来,在拍摄了多部短剧后,他有望成为一位头部短剧导演。为了事业,他在郑州租了房子,把孩子带到这里上幼儿园。也可以说,在短剧这条闪烁金光的产业链上,面包超人导演获得了一个舒适的位置。
面包超人导演每个月拍三四部短剧,这还是有意控制后的结果。他已经学会通过剧本的字数来判断工作量,以前没经验,接了一个看着像60集的本子(其实有100多集)。他按正常6天时间拍,每天拍到凌晨三四点。制片定宵夜的时候都咬着牙。
我们所在的芳华长歌影视基地藏在一间半开工的厂房里。要绕过两片长满杂草的巨大荒地和沿路的吊机、起重机之后,才能见到一片毫无气势的白色铁皮棚。关于这里的故事没人能讲得太清楚。有人说是厂房效益下降,有人说是一所培训学校改建而成,曾经的学员宿舍上下铺换一套军绿色的被褥,就变成了置景中的“监狱”,墙上贴满“珍爱自由”“好好改造”。不同的剧组在这里同时开戏,“监狱”的栅栏铁门外是“医院”缴费大厅,对面则正在开招标大会,高脚杯里摇晃着没汽了的可乐,所有人的手机突然中了蓝色骷髅病毒。玻璃格子间里,男主角和女主角坐在床上,深情款款地说着什么。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画面除了片场,大概只能在梦里见过。

芳华长歌影视基地外的荒地
短剧不负责真实和复杂,这一点所有拍短剧和看短剧的人都心照不宣。渣男脸上永远焊死一副金丝边眼镜,小三一定把大波浪头发梳到一边,再穿上性感的包臀裙,扭得矫揉造作。化妆师蓬蓬满脸怨念地说,凌晨三点就开始化妆,一个化妆间一早上送出七八个剧组,对他的考验是要用最破的化妆品化出最浮夸的效果,并能牢牢扒在脸上超长待机18个小时。长剧里惯常的化妆习惯在加厚柔光滤镜之下就是素颜。“一米多高的颅顶,平地起高楼。就是要好看,死人也要好看,那么长的眼睫毛死在那儿。”对短剧来说,一切都要显而易见、直击心灵。
就像短剧里千亿身家的有钱人永远都穿得blingbling。面包超人导演说blingbling材质和金扁担代表的意义是差不多的,都彰显了一种看客想象中的身份感。它不能是真的奢侈品,因为一部短剧的成本不过三五十万,“它的材质说白了就是聚酯纤维。”
造型师还会买来20块钱的5克拉大钻戒、比钻戒更便宜的奢牌包包,用双面胶把吊牌粘到裙子内侧,拍完了再七天无理由退回去。
浮夸的故事,浮夸的造型,它们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在于会有人“买单”。在片场,我和面包超人导演讨论了他的短剧的观众是谁,他是为谁在辛苦。
“下沉市场”,面包超人导演说,“下沉到下面老百姓看,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乡镇县。”
但这还不够具体,旁听对话的场记补充道,“就是那种大妈大爷平时在家没事刷着玩的。”
面包超人告诉我,这也是郑州的优势。南有横店,北有郑州,但横店以古装为主,郑州则有一种接地气的现代感,这里不需要沙滩游轮飞机,那种真正的富豪式的生活,真正优越的场景,郑州也没有,这里适配的是,老百姓朴实的吃喝拉撒情情爱爱。面包超人导演提到了杭州,他说杭州也不如郑州,因为“杭州拍出来场景什么的,感觉还是高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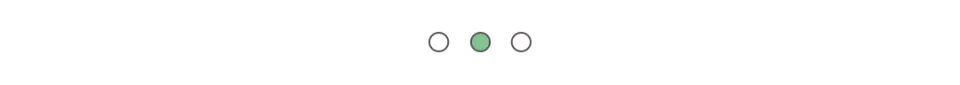
我就爱看这个
“停!太假了,什么玩意儿?你感觉搁那啃红薯一样。”面包超人导演看着眼前热吻的“渣男”和“小三”。他恨铁不成钢地扯下耳机,指导女演员把贴了精致美甲的手慢慢地漫上男演员的肩膀,要演出那种烈焰缠绵的张力,别像鸡爪子一样。“野一点!现在没有欲望!”
剧本里,男演员压在女演员上方,“迫不及待褪下上衣,扯着她的脚腕拉向自己”。这一切发生在男主的妹妹流产大出血急救当晚,而他是当地最好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忙于和女人厮混,他错过了亲自抢救妹妹的时机,导致妹妹死亡。
“我嘞个豆!”跌宕起伏的拍摄过程里,男主哥望着剧本数度感叹:“这什么逻辑?这男的有病吧?现实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男主哥履历看上去挺光鲜:国外表演专业毕业,演过不少叫得上名字的电影,还拍过央视的大剧。这是他拍的第三部短剧,第一部戏里,他演了霸总,台词不超过一百字,用他的话说,就是太轻松了,和玩儿似的。相比长剧动辄几个月的项目周期,短剧性价比颇高,一部戏的间隙里已经接到新的剧本。这一部杀青,立刻赶到下一部定妆。
我试图和男主哥搭话,他对我的好奇表示费解。“为什么想来了解短剧?”他问。我说,因为觉得短剧代表了我们时代某种现象。
“时代什么现象?”男主哥自问自答,“短平快。”他说现在的观众越来越要求快节奏,看一部电影很慢,看一部剧很烦,有时候看短剧都是1.5倍速。他承认这是时代的趋势,但他自己从不看短剧,包括自己演的这些。
那为什么还来演呢?男主哥说,因为他有孩子了。

芳华长歌影视基地外的荒地
但对很多人来说,短剧无疑提供了难得的向上通道。在片场,我遇到了男二号,一位反派专业户,同时是人生经历丰富的00后:据他说,他学过汽修,干过直播卖女装,在野鸡大学学过表演,还考过县城公务员。失败之后,他被一位在街上偶遇的短剧导演认定为“骨骼清奇”,邀请试镜,一年就从群演干到了男二。他的话真假难辨,但无疑带着一种普通人成功之后的自得之意。他告诉我,这部戏拍完,他就要赶去同在郑州的下一个片场,为此甚至耽误了爱情。
我还遇到了一个男孩。他97年出生,已经到了自认该谈“现实”的年纪。他在剧中出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学音乐的,主攻歌剧,毕业后在培训机构上班,但今年的招生相比去年直接减半,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在郑州拍短剧,然后某天看到她发了朋友圈——“三个月就干到女二了,我靠。不行我也干了。”
这大概就是身处行业上升期的魅力。
闲聊结束,拍摄继续。基于顺应人性的考量,在激情之外,剧本里安排了一场当街打小三的戏码,面包超人导演乐呵呵地说:“人民群众最爱看这个。”
这大概是一场真正的武戏。面包超人导演几度喊停,嫌“大妈”群演们下手太轻,要求其中一个把女演员的衣服使劲往下撕扯,露出肩膀。另一个拽她的头发,把精致的侧分大波浪弄乱。又要求务必在混乱中拍清楚女演员的脸,这是一张耗费数小时,用亮晶晶玻璃唇、巨大的钻石耳坠细细装点出来的脸。“别低头!这样怎么拍到你!”他不耐烦地喊,“快点,天光要没有了。”
打小三的热心群众们扯掉了这位女演员数根头发,半边耳环不知所踪,让造型师大为光火。她质问女演员,那只耳环没找着,后面接戏怎么办?你想过这个吗?人类的悲欢的确是不相通的。另一边的灯光指导看起来五十来岁,穿一身黑衣,很少讲话,总是戴着耳机稳如洪钟地坐在监视器前。他是导演也尊敬叫“大哥”的前辈。此刻,“大哥”少有地露出嘿嘿的笑容,操着一口地道河南方言乐不可支地说:“我就爱看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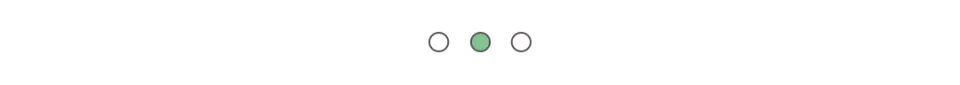
人生如戏
剧组是个江湖,来的人各有各的身份,但大抵都为一个钱字。外联老徐过去是个焊工,也卖过几年建筑机械设备。天天和钢铁照面,身上落下不少毛病。副导演小武卖过手机,开过快递驿站,结果还是黄了。制片老林当过民警,后来跟着哥哥做制片,曾经参与过几部著名电影,是剧组的“大保姆”。“没有我搞不定的事儿,知道吗?”他说。有一次演员在没通下水的样板间马桶里撒尿,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气得歇斯底里,一边亲自撸起袖子擦了好几个小时。
这里还有收不上物业费的物业经理,没活儿的婚礼摄像,毕业即失业的应届生,影视寒冬里出不了头的长剧演员……我遇到了一位演员助理,刚毕业几个月,志向是当短剧导演,但现在主要负责服务签约的女演员,拍照修图。短剧熬人,她也得跟着熬,熬过通宵,上一个剧组刚结束就进了这一个,繁重的工作把她搞得心烦意乱,“好累,我不想赚钱,我觉得现在累死我了。”
但也有人充分利用着其中的机会。“群头”兼副导演振彪总穿灰西装和锃亮的黑皮鞋,脖子上戴一个长长的木头珠子串,把头发精致地梳到一边,看起来很有些成功人士的味道。过去他在批发市场做过服装档口,还开过电商公司,后来开始当群演,一个月后就成了群头。这无疑算是一种青云直上。“群头每个人都想做,就跟男主一样,但是不一定你想就可以。”他说起话来掷地有声。
我目睹过他是如何抓住机会的。那是一次临危受命,一个男演员总是记不住台词,从下午拍到半夜,越说越不顺,导演开始摔东西骂脏话,顺便叫来当时在做副导演的他,让他不光把男演员,也把台下笑场的女群演一起开除。
情况紧急,他甚至来不及去化妆间,现场把外裤脱了,换上戏服,说:“我上。” “能不能行?”导演已经濒临崩溃。几分钟后,他中气十足的声音在片场响起。
所以包括我和大部分群演在内,在他眼里都幼稚不堪。“假如说我能干你这个工作,”他对我说,“两个月,我绝对,百分之百做到主编。”

聚美空港竖屏电影基地
他很有些活络的头脑,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前一阵,他搞了个表演培训班,交999元课程费,请老师来教,承诺每月推荐3-5个特约演员的名额。这个培训班预计11月底开课,但一个月过去也没有声息,群里8个人,3个是管理员。
但群演老虎还是交钱加入了。“干啥不投资?”老虎38岁了,仍然是一个温和近乎天真的人。我问他怎么不怕被骗,他犹豫了一会儿,“之前一块当群演的时候,我们坐过一趟车。”
老虎毫无保留地向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生存资源。认识不过几分钟,我就被他拉进数个通告群,只因为提了一嘴想找群演的工作。群里最常出现的数字是110/8,意思是每天110元,8小时,超过一小时加10块。一些更积极的群演会注明自己“无门禁”,意思是拍到几点都可以。
群演之上是特约演员,根据台词和戏份的多少划分为小特、中特、大特。小特的价格通常在“半二全三”,也就是6小时以内200元,超过6小时300元。中特半三全五,大特半五全八。再往上走,价格开始上千,最头部的爆款主演一天甚至能拿到两三万的高价。
老虎的梦想是做个在剧本里有名字的人。他打开自己的简历给我看——姓名:老虎。视觉年龄:35。身高:177。体重:145。“听话,事少,不墨迹,能吃苦,热爱影视,希望能加入贵组,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在作品栏里,他饰演过的角色分别是宾客、股东和记者。最新扮演的是领导,主要工作是拍桌子瞪眼,大喊“胡闹!”并带领领导二和领导三给主角团添乱。
老虎现在还背着十几万的债,他学画画,十几岁从老家洛阳跑去杭州,给纺织品做花案设计,一个月赚两千块。08金融危机那一年,杭州下了好大的雪。时代的寒潮袭来,穷得叮当响的老虎跟着亲戚飘荡去了新疆一个遥远的镇上干装修,每天骑着三轮车去给人装玻璃门。他在那里待了十多年,开过自己的店。他动手设计店里的桌子、茶几和电视柜,用刀在玻璃上一笔一笔刻出图案,焊接好楼梯,把养得毛茸茸的松鼠画到墙上。疫情来临,他关了店,把所有的东西装上小货车,带着小猫,还拉了两袋新疆的面粉和西瓜,先去老婆的故乡青海。开过艺考培训班,赔了钱,又辗转洛阳,来到郑州。一边接些几十几百块钱的画图订单,一边当群演。
这里有很多像他一样中年失意的人。开店倒闭的人,打临时工为生的人,迷茫的人。他试图活得更明确一些,赚钱还账,努力接活。通过画画,老虎觉得自己悟到短剧里的好多事。“股东,宾客,这不今天演了个领导,还演过警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都是现实中的一个翻版再现,就跟画画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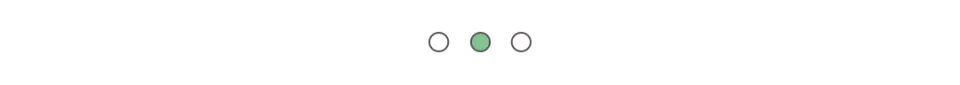
短剧把郑州的烂尾楼带起来了
就像我曾预计的那样,在影视基地拍摄之外,剧组开始每日“打卡”城市中的烂尾楼盘。我们来到一处废弃的售楼部,这里空无一人,超市、咖啡店、水果店样板间一溜排开,看起来已经上锁很久。“里面啥都没有,也没有真正开过,就是让买房的人看到未来的商业规划。”无疑,所有的规划都落空了。面包超人导演告诉我,“这个场景特别便宜,旁边还有一栋别墅样板间,里面有平层,我们后天还要来这边拍。”
剧组的车继续往城市边缘开。另一天的拍摄在一个空荡的小区,2016年左右开盘时,小区均价一度上万,但由于入住率不足50%,暖气公司拒绝供暖。高档小区身价倍跌,有的已经缩水一两百万。但对于短剧剧组来说,这就是拍都市剧的天选之地。
剧组委托物业来租借房间,61岁的陈姐最初不甚乐意,当初买下它是冲着边上雁鸣湖的风景,想为自己养老打算。屋里一米多高的花瓶、“厚德载物”的书法、雕花木书柜,甚至一坨沉甸甸的大玉玺,是旧身价的证明,但退休后没有暖气的现实,让她一天也没来住饼。她学法律出身,爱读书,看悬疑剧,嫌短剧情节太假、太粗糙、“太过弱智”。“给这几百块钱,我丢一件东西也不值几百块。”
在剧组来之前,陈姐对短剧的认识来自58岁的妹妹。妹妹甚至愿意为短剧付费,最爱看重生复仇、手撕渣男。这最终让陈姐同意把屋子租借出去。姐妹俩带着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开了40多公里车,从郑州市区来到这里瞧热闹,结果足足五个小时后才等来姗姗来迟的剧组。陈姐隐隐有点想发飙,但妹妹已经开始兴奋地往摄像机后面挤,她告诉姐姐:“幼稚是幼稚,但是很过瘾啊。”
而陈姐的房子,今天剧组拍完,已经又被另一个剧组预定了。
又一天,我们来到郑州海宁皮革城。难以想象过去这里有多么热闹,四层楼的皮革城曾经有几千家店铺,一个店面要卖三百万。浙江海宁人陈杰克就是那个时期来到郑州的,游客被大巴车、私家车一车车拉进这个“4A级景区”,他的小皮具店动不动一天卖出几万块,四五个服务员同时运转,客人多到连吃饭时间都没有。“那时生意真好做啊。”连周边的房价也一度高到一万六七千一平。
但如今,这里租金降了一半,还在营业的店只剩几十家,皮革城外,跑出租车的大姐指着空旷的大路对我说,你看,连公交车上也没有一个人。陈杰克招呼着店里仅有的客人,也就是我,希望多卖出一顶水貂毛帽子。
是短剧拯救了皮革城,如今四楼整个被改造成短剧基地。空店铺被置景成“中医馆”,里面满满一面墙的中药柜图案。而曾经人来人往的过道,被低成本改造出了一个机场造景:只需摆上椅子和“国内到达”“行李查询”的指示牌。

郑州海宁皮革城被改造成影视基地,但仍有大量商铺空置
只是短剧没法拯救原本的小生意人,陈杰克已经关了几个店。也许很快也会离开这个地方,去寻找新的水草丰美之地,如果它存在的话。
在郑州,我还遇到了一位原本的房产中介,他入行十年,经历了郑州房地产的数个波动周期。在21世纪10年代,被称为“国际郑”的郑州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项目总是开盘即清。开盘前一晚几百人连夜排队打地铺。他告诉我,为了抢一套房,人们甚至会在现场打架,售楼部的门被挤掉都是常有的事。
只是后来,他所在的房企6个月发不出工资,他离职了。落寞和热闹在人世间恒常地反复,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一位朋友带他去客串过短剧群演,演的是一个反派人物的小弟,穿着和房产中介差不多的黑色西装。一天300元,现在早已没有这个价格了。
那天下着雨,拍摄现场就在一个空置的售楼部。捱了一个下午,也没搞懂剧情到底是什么。他感到一种失落。“之前这么轰轰烈烈的售楼部,现在都被短剧占领了。”他想,“人生就是这样的。也正是无常,所以也充满了机遇。虽然大环境在这,但是能怎么办?继续努力向前。”

一处荒废售楼部门口正在拍摄的短剧剧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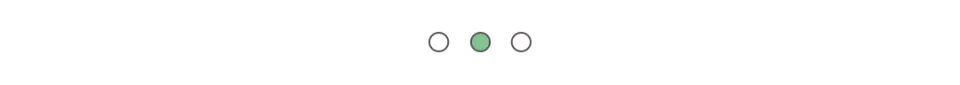
卡钳
“你有没有发现前10集的戏会拍得很细,然后时间会很长?”剧组里一位演员向我传授短剧拍摄的秘密,前10集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第一卡点,又被称为“卡钳”,要像钳子一样钳住臂众的目光,“第一个卡点是什么意思?最主要意思就是到第一个卡点了,大家要充值交费。”
我旁观了一场墓地的戏,面包超人导演觉得去真正的墓园太远。一来一回,三个小时就没了,“三个小时,我能拍多少东西?”他决定在酒店楼下大路中间的三角区挖个洞,埋上泡沫板墓碑凑合一下。拍摄途中,附近的村民带着几个孩子来看热闹,三轮车时不时从旁边驶过,留下一张张疑惑的脸。
我也在想,这场戏到底属于前十集的“卡钳”还是以后的?
在郑州,人们告诉我,短剧行业已经经历了四个时代:短剧1.0时代,郑州因比较优势脱颖而出:低廉的场地费用以及人口大省带来的低成本人力,那时狗血是主流,粗制滥造是常态,最高级的技巧就是镜头进场“旋一圈”。
然后是2.0时代,红果、河马等大平台进场,短剧受到巨头青睐,获得了流量扶持,在全国范围内红火起来。3.0时代,则是日益正规化,官方引领,文旅支持,地方政府开始以优惠的地价招商引资,各类拍摄基地开始涌现,它们构成了一座座“短剧工厂”。然后,就来到了4.0时代,从2025年开始,短剧赛道竞争加剧,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头部明星开始涌现。而成本也就水涨船高。整个行业蒸蒸日上,但从业者赚钱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一些短剧公司开启了AI动态漫剧的制作,这能省下演员的酬劳。

皮革城里的短剧展示
对面包超人导演来说,短剧行业的“升级”,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他接到噩耗,自己的下一部剧发生了“炸组”:原定的男主不演了,临时换上新演员,女主又不干了,“粉丝量不够,她不愿意跟他搭。”按他的说法,这是把长剧的毛病带进了短剧。
在郑州的最后一天,托面包超人导演的福,我如愿当了一次群演。副导演小武带着他当过舞蹈演员的徒弟阿雷,挑挑拣拣几天,给我安排了一个患者的角色。阿雷很认真,提前嘱咐我准备一双拖鞋。但到了第二天,在现场的手忙脚乱里,我的角色临时换成了护士,负责给“尸体”盖上白布。
化妆师蓬蓬帮我盘起头发,用定型喷雾和摩丝把每一根乱发收拾熨帖,直到我的头发摸起来像一块硬邦邦的橡胶,再拿黑色发卡把护士帽固定在头顶。“我就说嘛,你也不演一个。”他一边弄一边说。
从穿便装到有了造型,我顿时产生一种“升咖”的感觉。
但片场突然传来一阵骚乱,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造型师已经一个箭步冲到面前,开始拆我的头发。“你去顶上吧,哪里需要哪里搬。”面包超人导演笑嘻嘻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因为统筹不当,作为“尸体”的女三号提前离开了片场,下一场戏紧急需要一个“尸体”替身。我迅速被换上一身病号服,头发拆开,硬邦邦地垂着,就这样从安置“尸体”的人变成了“尸体”。一块蓝色的无纺布盖在我的身上,我僵僵地躺在那儿,能看见无纺布的缝隙里亮堂的手术室大灯。几个群演扑在我身上痛哭失声,像是真正失去了亲人一样。“咔!好,过了。”我从床上爬起来,人们已经面无表情地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