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图灵不是一位好棋手
2025-09-07 04:25:38 · chineseheadlinenews.com · 来源: 量子位
咱就是说,还好祖师爷图灵不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
不然整个世界的AI发展脉络以及技术进展速度,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看到这儿有的人可能犯嘀咕:不是,为啥这么说啊??
国际象棋不是和AI关系密切,从计算机科学发展之初就相互促进,共同演进吗?
注意了,这句话的重点在于:还好图灵不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
如果他是个大师的话,可能就专精棋艺,不一定会被选中召去布莱切利庄园(英国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中心)。
当然,图灵也有可能还是被选中去布莱切利庄园工作。但就不会因为棋艺不佳,只能常常和水平旗鼓相当的唐纳德·米奇(Donald Michie)对弈。
二人不仅成为好友,还合作了博弈树算法——这成为后来AlphaGo的核心。
两人每周都会一起下棋,并且因为下棋时的闲聊,对后来的AI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如果当初图灵棋艺高超,下棋的对手不是米奇,很多历史,可能就此改写。
好了,我们现在详细来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人菜瘾大”的国际象棋棋手图灵
图灵会下国际象棋,爱下国际象棋,这事儿声名远播。
但有的人可能不清楚,图灵的国际象棋棋艺水平算不得高超,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有一些平庸 (doge)。
这里和大家分享分享一则闲闻轶事——
1939年,正值二战爆发前夕,英方急需破解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以获取军事情报。
因此,不少在密码破译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才都被召至了英国政府密码学校的所在地,也就是布莱切利庄园。
图灵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那儿工作了好几年,在此期间发明了举世闻名的图灵机。
以上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布莱切利庄园时期,除了潜心研究密码破译等相关工作,图灵最爱的事情就是和同事来几局国际象棋。
当时图灵的同事中不乏一些知名的国际象棋顶级大师,比如休·亚历山大(Hugh Alexander)和哈里·戈隆贝克(Harry Golombek)什么的。
和他们相比,图灵是什么水平呢?
据传某一次对弈过程中,图灵给自己下成了死局,死活破不了。急得戈隆贝克把棋盘转了一百八十度,自己动手来帮图灵挽回局势。
显然,和碾压式的对手下棋不是长久之计。
图灵很快为自己物色了一个更合适的下棋搭子,18岁的唐纳德·米奇。
米奇没啥数学背景,但是学习能力很强,学东西很快,后来成为了布莱切利测试小组的关键成员——测试小组选拔的人都是具备横向思维、模式识别和逻辑推理能力的精英。
在测试小组工作期间,米奇和图灵成了好朋友,甚至离开布莱切利庄园后,两人还长期保持联系。
最关键的是,因为两人在国际象棋方面的造诣差不多,棋逢对手,顺理成章成了下棋搭子。
每周,两人都会在布莱切利庄园不远处小镇上的酒馆里下棋。
后来米奇回忆说,边下棋边闲聊的时候,他们俩聊的话题常常围绕“学习型机器(learning machines)”和“机器下棋”(mechanising chess)等展开。
米奇表示:
对我来说,这些谈话对我在机器智能领域的探索起到了启蒙作用。
受此影响,米奇成了AI研究先驱
二战结束后,天才们纷纷离开了布莱切利庄园,但米奇对机器智能领域的探索没有结束。
过了几年,米奇和人合作了一套纸上机器(即没有任何硬件和软件,仅用纸笔模拟机器运作逻辑)的下棋算法,名叫MACHIAVELLI。
这套算法的核心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即根据对手的走子选择下一步棋怎么下。
Be like:
输入:对手走了什么棋
中间:按照一套写在纸上的规则判断局势
输出:决定下一步走什么
这个策略和他在布莱切利庄园破译密码时的思路如出一辙,都是用“受限搜索”的方式来缩小可能性。
而图灵发明的Bombe机,用的也是这套思路。

△图灵和Bombe机(AI绘图)
提一个小插曲,米奇的这套算法后来被另一个同仁点名批评。
1948年,当年同在布莱切利庄园工作过的杰克·古德(Jack Good)——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国际象棋大牛——去了趟牛津,旁观了米奇演示MACHIAVELLI。
一周后,结束旅程的杰克给图灵写了封信,信里指出了MACHIAVELLI的缺陷。
只会“走一步看一步”。
杰克觉得这套算法一定是个臭棋篓子,即使能非常准确的评估位置,但棋局一旦复杂化,它就很容易抓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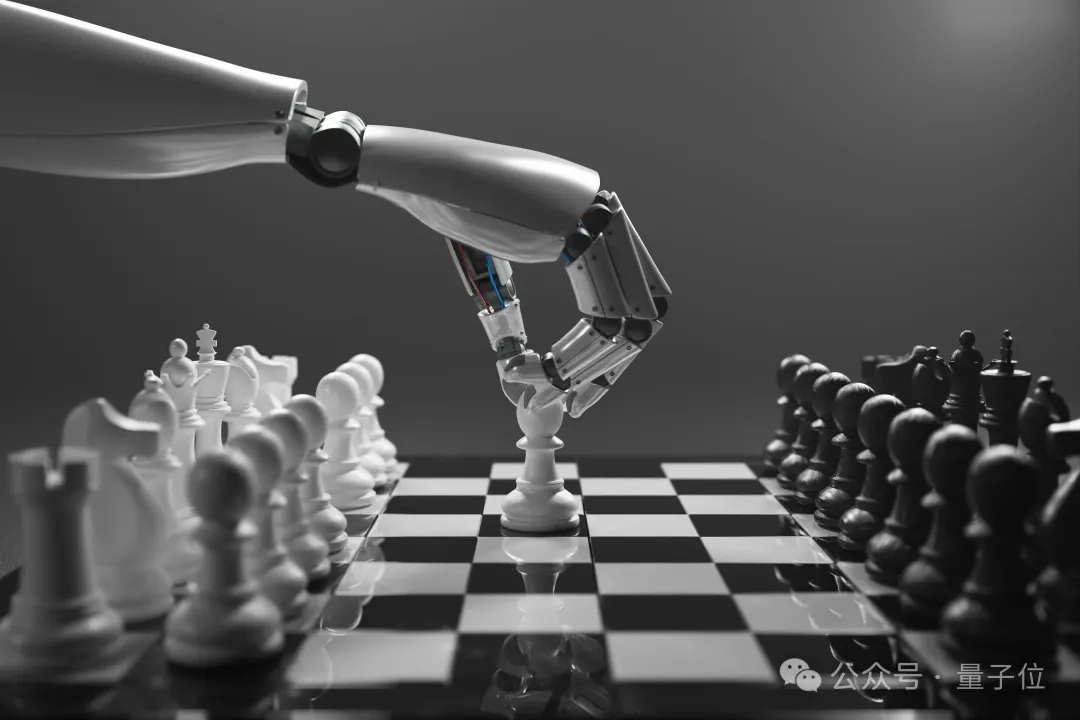
不过,这种试图缩小范围,通过启发函数选出最佳答案,而不是穷举的思路办法,后来被命名为“启发式搜索”,并被广泛使用。
启发式搜索突破传统的暴力计算方式,实现AI的智能决策,解决了复杂问题的计算可行性。
现在,它其实已经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导航、物流、游戏规则制定、AI诊断等。
1960s,米奇还和詹姆斯·多兰(James E. Doran)依据启发式搜索开发了图遍历程序(Graph Traverser Program),解决从起点到终点的最佳路径问题。
其逻辑结构,奠定了AI中路径规划、博弈搜索、图像识别等基础。
“研究计算机下棋,并不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同样是1960s,米奇在在爱丁堡大学创立了机器智能与感知系(Department of Machine Intelligence and Perception)。
这里逐渐发展为欧洲最重要的AI研究中心之一。
到了70年代,由于AI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批判性文献《莱特希尔报告》的发布,英国AI研究的经费被大幅削减,米奇的研究也受到了限制。
但他继续用有限的资金对国际象棋残局进行研究。
米奇适始终坚信,国际象棋在AI研究中十分重要,如他在《国际象棋残局模式知识的表示》的草稿中明确提到的那样,“研究国际象棋并不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没有其它同样合适的材料可以用来研究某些重要的科学问题”。

中途有一段时间,米奇转型成了遗传学家,但他始终没有离开AI研究。
而国际象棋几乎贯穿了他整个AI研究生涯。
他在一篇论文里进一步说明,这种策略游戏适合AI研究及其主要优势:
国际象棋是一个定义明确且规范化的领域。
它挑战着各种认知功能中的最高智力水平,包括逻辑概念形成、计算、死记硬背、类比思维、演绎和归纳推理等等。
USCF评级系统提供了一个普遍接受的绩效数值标度。
这个游戏可以轻易分解成子游戏,这些子游戏可以接受密集的单独分析。
对米奇来说,国际象棋不仅仅是一种方便且有趣的探索机器智能的方式,更是AI研究中的“果蝇”,完美适用于“研究机器中知识的表示和测量”。
米奇的观念影响了许多后来者,其对国际象棋残局的研究,在70、80年代许多项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的博士生罗斯·昆兰就受此影响,后来开发出了ID3决策树学习算法。
这是CLS开发的一系列程序之一,旨在应对米奇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归纳任务。
即仅根据基于模式的特征来判断在固定的移动步数内,“国王-车”对“国王-马”残局中,马是否处于劣势。
昆兰曾在论文中特别致谢了国际象棋棋局。
One More Thing
如果当年图灵是个顶尖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可能后来的一切都会不一样。
蝴蝶效应嘛~
但现实的发展就是,国际象棋背后的许多东西都予以计算机科学乃至如今的AI以启迪。
而且学习国际象棋,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培养一个人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和做决策的能力。
不过,和深蓝大战三百回合的历史最伟大棋手之一卡斯帕罗夫曾表示,“一个人擅长国际象棋,并不意味着你在其他领域也特别出色或擅长”。
现在,由于生成式AI时代的到来,大家对国际象棋水平和AI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
Hacker News上有网友讨论分享了ta的亲身感受,那就是国际象棋的高分选手可能逻辑上面真的很差。
还有网友表示,现在大家追求的AGI,既不擅长下棋,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善于伪装成人类。
所以我们追求的AGI,到底是什么啊?